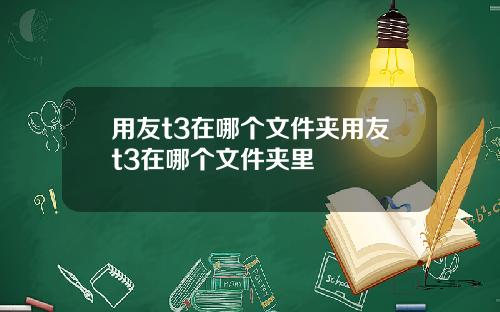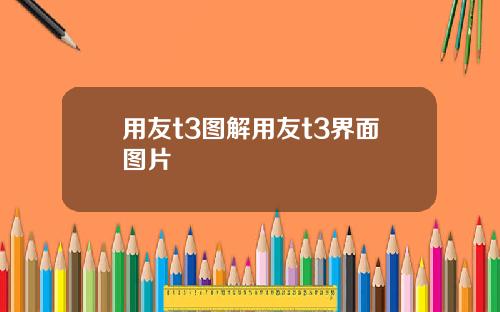【推荐】中国需要织起合成生物领域的安全屏障辉瑞收购千林花费多少
本文转自作者 | 王英良
生物合成可能产生伦理道德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社会风险以及国家安全风险。合成生物的兴起使中国生物安全屏障更面临挑战。
合成生物是将生物科学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崭新生产方式。合成生物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生物能源、绿色制造、农业制药、人造生命、食品和发酵工程等领域。作为一种新的工艺,其重要性日渐被人所熟知。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认为,合成生物学将颠覆传统行业。从科学角度看,合成生物学技术已逐渐走向成熟,成为有竞争力、具有可持续性,理论上可以生产近乎任何产品的生产方式。合成生物学的发展,有望使产业链不再受原材料供应限制,企业可以从头开始,利用细胞设计制造无限量产品。合成生物学成为催生生物经济的颠覆性力量,或将科学转变为未来的制造范式。理论上,微生物可以制造许多目前在用的工业品,因此合成生物学提供了生产香料、纺织品、食物、燃料等几乎所有人类所需产品的新方法。目前,不少合成生物初创企业已经瞄准化工、制药、疫苗、食品、纺织等行业。从中期来看,以传统方式运行的这些行业将面临来自合成生物替代品成本优势方面的竞争;从长期来看,矿业、电力甚至建筑等行业都将面临竞争。合成生物学是人类生产方式的革命,当然在巨大机遇面前,也要正视潜在的风险和挑战。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代表性私营公司有凯赛生物、华恒生物等,而国家队则相对庞大,实力雄厚,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研发中心。相比于欧美在合成生物领域有较长的历史、专利积累以及较完善的金融支持不同,中国合成生物产业化阶段时间并不长,目前还处于融资形成“独角兽”阶段。今年6月,依托清华大学科研技术,清华教授于慧敏旗下衍微科技宣布完成5000万元人民币的天使轮融资,由红杉中国和峰瑞资本共同领投,水木创投和康裕资本跟投。无独有偶,在去年7月,合成生物技术开发商恩和生物完成1亿美元B轮融资,投资方是红杉资本中国(领投),招银国际、源码资本、经纬中国、夏尔巴投资、五源资本、美团等。其中,红杉资本是典型的美国风投基金,沈南鹏是红杉在中国的执行合伙人,其长期经营中国,对中国新兴产业的反应相当敏锐。作为总部在上海的跨国公司复兴医药,亦相当关注合成生物领域。复兴本身是一个在跨国收并购和联合疫苗开发与医药大宗贸易走在前列的巨型企业。
实际看,外资在中国涉生物以及制药领域的收购迟早会转向对中国本土生物合成企业的收购,而中国本土的生物和化工企业也出现了向合成生物技术转向的趋势。由于产业历史局限,中国本土合成生物产业的基础集中表现为制药、化工两大方向。制药企业由于涉及敏感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其脆弱性更加明显。此前,外资通过资本杠杆基本完成了对中国本土主要医药产业面的收购、控制或具备稳定施加影响力的渠道。比如,2007年德国拜耳收购东盛“白加黑”、诺华2009年对天元生物的收购、2010年10月塞诺菲收购BMP太阳石、2010年11月奈科明收购广东天普、2010年12月葛兰素史克收购南京美瑞、2011年12月阿斯利康收购广东倍康、2013年2月利洁收购桂龙药业、2014年2月拜耳收购滇虹、2015年11月卫林收购辽宁天医、2016年辉瑞收购千林健康。可见,一些知名的中国医药企业事实上是外资在华子公司。
另一个杠杆是股权。在合资领域,早在1992年昆明制药集团就与美国IVAX下属BakerNorton制药成立合资公司——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1993年印度南新与白云山药业实现合资;2009年6月发生葛兰素史克与海王生物成立合资公司;1995年法国塞诺菲与民生药业成立合资公司;2001年印度阿拉宾与山西威奇达成立合资公司;2009年10月葛兰素史克与江苏沃森公司组建合资企业,研发并生产面向中国市场的小儿疫苗;2009年11月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制药公司,以8.5亿元人民币收购浙江天元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85%的股权;2011年默沙东与先声药业成立合资公司;2011年9月瑞士龙沙与复星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2012年2月辉瑞与海正宣布成立合资公司,辉瑞占股49%;2013年5月安进与贝达宣布筹建合资公司;2013年12月印度熙德隆与辅仁药业筹建研发基地;2016年参天制药与科瑞药业实现合资;2016年12月华润与赛诺菲签署战略合作意向等。一些拥有合成生物技术的新兴药企,也积极寻求资本市场融资,这意味着外资可能有渠道获得某种控制权。
作为一个较新的领域,生物合成可能产生伦理道德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社会风险以及国家安全风险。一个挑战是,中国在生物安全防御原本薄弱,而合成生物的兴起使生物安全屏障更面临挑战。目前看,中国主要制药以及生物公司普遍有外国公司参与,在合成生物方兴未艾的背景下,生物制药、化工等将出现新的革命。新的生产工艺带来的风险是显而易见得,比如,通过医药市场流通,受污染或有毒的疫苗通过注射其有毒成分可能永久存在人体内,但由于致病周期比较长,事故的司法循证可能变得相当困难,这也导致针对外国跨国公司的司法调查需跨国协调。在如此密集的外国控股和中外合作背景下,在商业利益的眩晕迷雾下,如何排除外国公司可能构成的生物安全威胁?比如,以生物攻击手段或以实验目的的制药公司以技术失误为借口造成社会面上的危害,而中国政府却难以施加制裁。如何排除这种成本极低但危害长远的风险?目前,还没有出现明确的社会危机警示信号和审慎的风险防范讨论。
合成生物领域已经逐渐受到中国国有以及私营生物医药、化学公司的青睐,这不仅表现为研究机构的兴起,也表现为市场融资、企业高薪招聘相应领域人才,部分头部企业市值水涨船高等。如果说生物欠防备使中国已经吃了不少“哑巴亏”,一些有毒或被污染或受到基因编辑的有害疫苗没有得到应有的警惕和司法制裁是“过去式”的话,那么从过去的系列制药和疫苗问题中汲取教训,在合成生物领域织起新的安全审查和防御网络就有其现实的必要性。
国家间的竞争无处不在,一个事实是跨国公司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执行国家产业和安全政策的重要媒介。中国要从现有的生物安全防御与时俱进地扩大到涵盖合成生物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威胁的应对上。对涉外资参与的合成生物产业规划要逐渐开启股权审查、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生物伦理调查、药品安全检查等。随着中国逐渐实施国际通行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规范,诸多领域与国际接轨是一种趋势,但在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合成生物领域,还需要实施对已有外资收购和并购安全的再审查,包括对涉生物合成技术产业的关联公司实施审查,对头部制药企业和涉药品进出口业务的跨国公司实施业务飞行检查。同样,在涉及中国具有一定竞争力但是具有一定排他性的中药及制品上,可以设立外资合成生物企业投资的“负面清单”,保护一批具有高经济收益和地理标志性的中药品种免受新技术的破袭就显得有必要。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逐步收紧在战略领域的外资收购以及从严审审涉“军民两用技术”企业的对外投资,因为直接投资意味着控制权的转移,要剥离这种控制权或采取回购或采用司法审判等手段,通常会产生一定的国际冲突。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博弈中,全球化有重新回归区域化、国别化的趋势,而合成生物技术显然是一种新兴的此前并未受到足够重视的新式“军民两用技术”,其更可能成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对此,中国要未雨绸缪、主动预阻相应的国家安全风险。
- 版权所属:金桔财经
- 文章作者:summer
- 本文地址:http://caijing.cj8835.cn/88307.html
版权声明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931614094@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金桔财经
金桔财经